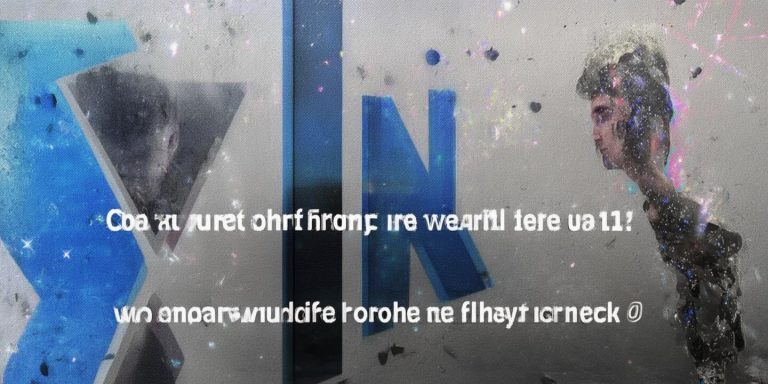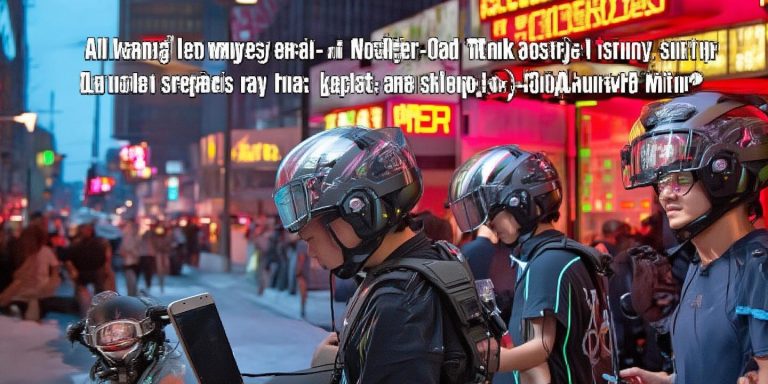天才与资本主义的交汇,往往诞生于最严酷的环境中。编者按: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研究所(ID:caijingyanjiu),作者叶子凌,经微新创想授权发布。在《三星帝国》中,李秉喆投资电子产业的转折点,正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。中东战争引发的原油缺口,让他意识到资源匮乏的韩国,或许该将未来押注在附加值更高的电子产业上。与韩国类似,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严峻——不仅缺油少矿,连水资源都成为奢望,更面临来自三个方向的阿拉伯国家威胁。以色列的发展轨迹与韩国惊人相似,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卓越。《创业的国度》序言中写道:我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资本,就是人。这片弹丸之地,人口不足千万,却诞生了世界十大晶圆厂之一的Tower Semiconductor(高塔半导体)、第二大FPGA芯片公司Altera,以及自动驾驶芯片巨头Mobileye,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位列全球第三。今年6月,以色列宣布英特尔将斥资250亿美元建设晶圆厂,这一数字接近美国《芯片法案》补贴总额的一半。不久前,英伟达也宣布在以色列建造AI超级计算机,并与800家初创公司、数万名软件工程师合作。饱受战火与仇恨蹂躏的土地,为何成为半导体企业的必争之地?

上过前线的企业家

1967年6月5日清晨,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埃及空军基地还进行着早班交接,以色列战机突然从上空扫射机场跑道和战机。地面部队同时向埃及西奈半岛发起进攻,特拉维夫的8200情报部队也在后方展开行动,截获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保密电话,掌握了阿拉伯联军的计划。这场仅持续六天的战争,以以色列的压倒性胜利告终,被称为“六日战争”。战争首日就立下大功的8200,起初只能使用美军淘汰装备。战后,8200地位迅速提升,开始快速发展。

由于被阿拉伯国家包围,以色列是全球少数实行全民兵役制,女性也需服役的国家。8200从每年新兵中挑选百名技术人才,进行计算机编码、黑客技能培训,负责情报搜集与破译。五次中东战争后,大规模冲突虽已平息,但技术进步从未停止。8200的另一重身份是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引擎,大量精英退役后投身商界。《福布斯》统计显示,超过1000家高科技企业源于8200部队。《创业的国度》中写道:在以色列,军队经历比学术经历更重要。求职时,面试官必问:你在哪个部门服役?

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,希伯来大学两位教授提出新计划:以色列必须掌握科技优势,才能弥补人少地小的劣势。战争中埃及的突袭让以色列措手不及,阵亡2800人并失去西奈半岛。美国调停后双方休战,但战争极大挫伤了以色列的自信,催生了Talpiot计划。与8200类似,Talpiot每年筛选2%顶尖高中生,经严格测试后进入军队专攻数理科学。顺利毕业者成为“Talpion”——源自圣经的城堡塔楼,象征至高成就。至今培养的650名Talpion,几乎都成为顶级学者或科技创始人。这种不计成本的军事投入,让以色列批量生产了高科技人才。

1974年赎罪日战争后,英特尔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投资者。英特尔在以色列北部的海法设立首个海外研发中心,负责人多夫·弗罗曼(Dov Frohman)毕业于被誉为“中东MIT”的以色列理工学院,后加入英特尔并发明了EPROM。这项能通过紫外线擦除数据的可编程存储器,使芯片可重新定制,为闪存技术奠定基础。戈登·摩尔曾称其重要性不亚于CPU。1974年功成的弗罗曼说服英特尔扎根以色列,海法团队在1980年设计出里程碑式的8088芯片,成为首款面向PC市场的CPU。1981年IBM推出搭载MS-DOS和8088的PC,获得巨大成功。以色列企业家甚至开玩笑建议英特尔将“Intel Inside”改为“Israel Inside”。随后英特尔在耶路撒冷建厂生产386芯片,海湾战争期间订单仍准时交付。以色列逐渐成为英特尔最重要的海外研发中心,英特尔在此投资并购愈加频繁,累计投资超30家公司,金额达数百亿美元。

英特尔带大的孩子

苹果设计A4处理器时,挖来了在英特尔工作十多年的Johny Srouji。这位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生,迅速成为苹果芯片部门核心人物,被彭博称为“最神秘的苹果高管”。活跃在以色列的芯片工程师多在英特尔工作后离职创业,再被科技公司收购。英伟达69亿美元收购的Mellanox就是典型例子。创始人Eyal Waldman在22岁参军后进入以色列理工学院,在英特尔工作五年后创办Mellanox,其infiniband技术因高吞吐量和低延迟,成为AI数据中心理想选择。2020年,英伟达、微软、赛灵思同时竞购,最终被英伟达收入囊中。其DPU技术源于Mellanox内部孵化,可提升AI数据中心网络性能。收购后英伟达将1000多名工程师纳入麾下,在耶路撒冷等地设7个研发中心,雇员近3000人。Waldman卖掉公司后专职做天使投资人,成为以色列科技公司的典型路径:大公司辞职创业——瞄准前沿技术——被大公司收购。

苹果在2011年收购的Anobit是类似案例。其闪存控制器技术主打低功耗、支持20nm以下制程,与苹果iPad和Mac产品线需求完美契合。收购目的耐人寻味。以色列公司常瞄准AI、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,技术成熟后寻求被收购退出,成为风险投资圣地。据统计,以色列1/3公司通过上市退出,2/3被美国公司收购。当技术人才走出军队和大学,美国公司已准备并购条款。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核心,是以教育系统和技术产业化组成的人才输送体系,榨干每个人的价值。方法不是强制加班,而是提升创造力上限,换取高价回报。
同一时期的日本和韩国
70年代,日本存储芯片超越美国,登上全球顶峰,但90年代衰退。韩国则通过产业政策主导的产学研合作,击败日本,保持优势至今。东亚电子产业依赖出口贸易带动的产业升级,高校批量培养理工科人才,支撑大规模标准化生产。技术进步集中在制造环节,核心竞争力是规模换来的成本优势。东亚经济体凭借强势政府、高储蓄率和廉价劳动力,成为摩尔定律的主战场。而以色列缺乏这些条件,选择了不同道路。越是前沿科技,个体越重要——比如苹果造芯的另一功臣Jim Kaller,在多家巨头留下传奇作品。2013年Geoffrey Hinton若加入微软或百度,深度学习历史可能改写。对2009年的苹果而言,Johny Srouji的价值远超10000名普通毕业生。以色列的思路:与其培养10000名合格工人,不如赌9999个人平庸,剩下的1个人就是Johny Srouji。
谢谢你,夏尔·戴高乐
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,法国突然中断对以色列武器供应,被视为以色列的“斯普特尼克时刻”。1960年法国承诺提供200辆AMX13坦克和72架“幻影”战斗机,但1967年转向阿拉伯世界。戴高乐继任者将坦克转给利比亚,已付款的50架战斗机转给叙利亚。《创业的国度》描述:法国背叛让以色列决心自主研发武器。虽然狮式战斗机项目取消,但失业工程师流入科技公司,自主军事研发经验间接推动了以色列集成电路技术发展。高科技突破有多种路径,但在以色列,它是战争阴霾、贫瘠土地、哈马斯火箭弹,以及对技术人才的极致汲取。投资ICQ的尤西·瓦尔迪说:以色列高科技的缔造者,是阿拉伯世界和夏尔·戴高乐,是他们逼我们发展工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