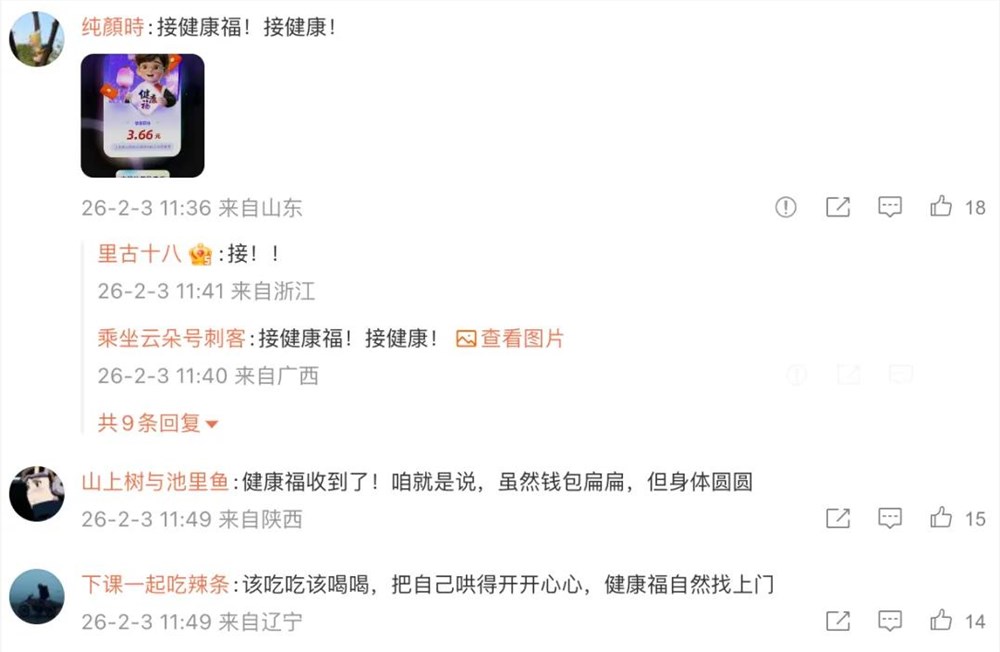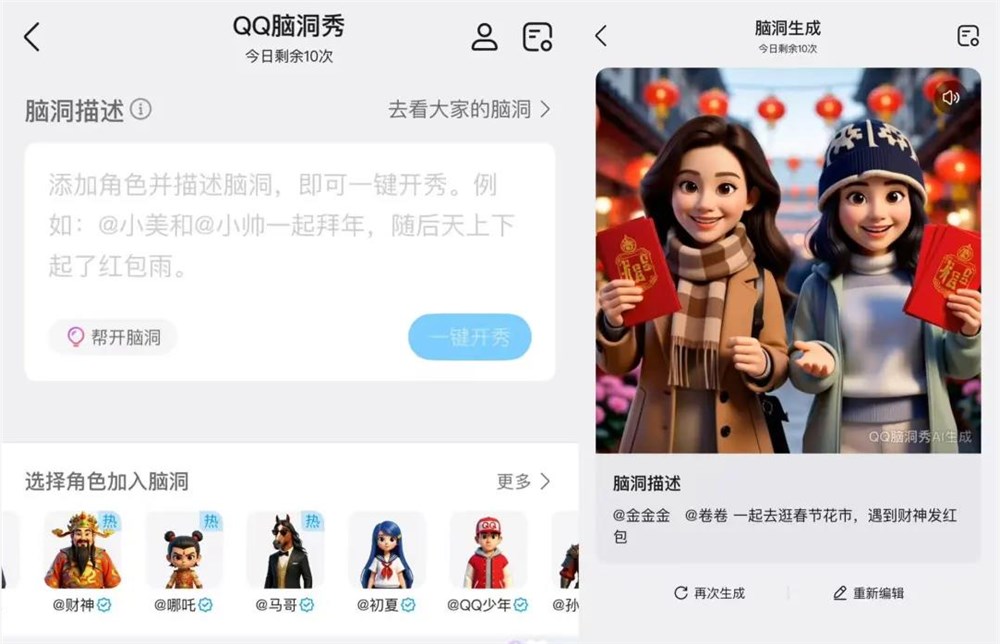可行走的街区才繁华
乍看起来,Citywalk似乎只是简单的”遛弯”,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区别。简言之,Citywalk的核心不在于行为本身,而在于体验。就像游客下乡采摘草莓,虽然花费时间、忍受辛苦,价格也比城市菜市场高,但真正重要的是获得的体验和意义感。这种现代Citywalk起源于英国,最初由专业讲解员带领,按照精心设计的路线,从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等维度感受城市风貌,在时空维度中沉浸式体验城市生命力。正如历史上许多事物进入中国后发生变异一样,英国的Citywalk到了国内呈现出不同面貌——既缺乏职业领队,参与者目的也未必是深度文化体验,发现城市特色反而在其次,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既时髦又浪漫,随意漫步就能获得情感满足。国内Citywalk最早在小红书兴起,不可避免地带上社群文化特点:分享体验时更注重拍摄美照,城市背景只是衬托个人气质,导致独立书店、特色咖啡店等”出片”地标频繁出现在路线中,甚至比老房子更受青睐。女性参与者显然更多,这与她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密不可分。
这项活动爆火的重要原因在于契合了当下年轻人需求。当前消费市场呈现”大件消费遇冷,小件消费兴旺”态势,经济压力下”诗与远方”变得奢侈,而Citywalk只需投入少量成本就能获得精神满足;对于暂时失业的年轻人来说,时间也不再是障碍。从某种角度看,这是一种”看起来很美”的消费降级式城市体验——在有限预算内重新发现城市魅力。但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Citywalk。北京因”宽马路、疏路网”设计让行人望而却步,而东京、纽约、香港”窄马路、密路网”模式更有利于商业繁荣和资本渗透。密如蛛网的小马路不仅便于步行,更因临街小店众多、移步换景丰富而吸引人,否则就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那条1.3公里长的全封闭边界,让人望而却步。成都空间设计师余明旻表示,他只在老城Citywalk解压,因为天府新区等新城虽然漂亮却”不可行走”——宽阔马路、单一景色、稀疏店铺让人失去漫步动力。随着新城发展,部分区域也开始变得适合行走,这种割裂现象在国内城市普遍存在。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宽达100米,视觉效果震撼,但步行体验远不如老城区——路宽、建筑单体大导致街景单调,最火爆的Citywalk路线都在老城厢。西安高新区经济发达但汽车导向,老城区因停车难被许多人忽视,却因丰富店铺小吃而更热闹。城中村同样具有这种特质,老西安认为”西安繁华在城中村”——卫生改善后,狭窄曲折的小路充满烟火气,生活成本低廉便利,各色人等汇聚于此。
为什么城区差异如此明显?关键在于老城和城中村是自发形成的复杂生态,自然满足多元需求;而新城多是规划产物,像功能分明的巨大机器。人类本能更偏爱有机体,Citywalk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。当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,街区”可行走性”变得至关重要——不可行走的街道难以产生”烟火气”。传统城市街道一味追求笔直宽阔,却忽视行人需求。适合Citywalk的街区不仅需要”窄马路、密路网”设计,更需要培育复合有机生态——建筑、店铺、人群、文化沉淀的多样性才能吸引人行走。简·雅各布斯在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中指出,新建市政中心容易排斥活力,而小马路、高密度街道更安全丰富。欧美近半个世纪的城市设计理念一直在反思”汽车导向”模式,因为道路被汽车侵占后,街道社会功能被抑制,城市被切割成碎片化空间。大卫·恩维齐早在1999年就指出,城市交通投入越多,交流空间就越无力,城市本质就越丧失。当代消费已从目的性转向无目的性,人们常在闲逛时偶然发现有趣店铺,这种”有惊喜”的体验正是Citywalk精髓。城市设计早已证明,当交通以步行为主时,活动领域与社会空间高度重叠,老房子、雕塑、茶馆等隐秘场所成为人们交流的理由。
北京中关村曾是人流混杂的热闹之地,后来大厂搬走、学校封闭,新修宽马路沦为”鬼街”。Citywalk不仅是个性活动,更可能重塑城市活力,引导客流,冲击商业生态。共享单车、公共交通等新技术手段将加速这一进程。消费本质是回应人心,所谓”烟火气”需要自发商业生态,而商业也需要文化体验赋予价值。新城区因街道宽阔难以复制老城夜生活丰富性,往往建造封闭单体建筑,成本高且生态封闭。欧洲许多城市通过封闭道路、创建自行车道、拓宽人行道收回道路空间,老城中心变得更宜行走,文化体验和商业生态随之繁荣。《城市设计的维度》指出,设计人们乐于使用的空间才是成功之道。既然Citywalk兴起,城市改造也应调整思路——拆除封闭门面、改造小路、扶持小商铺、降低开店成本,吸引人流回归。大公司也可考虑分布式办公,让市场销售等部门在老城办公,既便于会见客户,又能劳逸结合。单位若要封闭办公,必须承担全部生活成本,否则应尊重人们自由选择。哪些城市能顺应这一潮流,重建以人为本的城市生活体验,就能从中获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