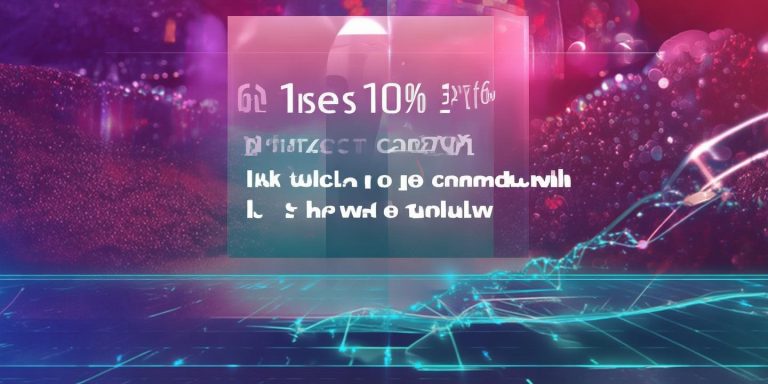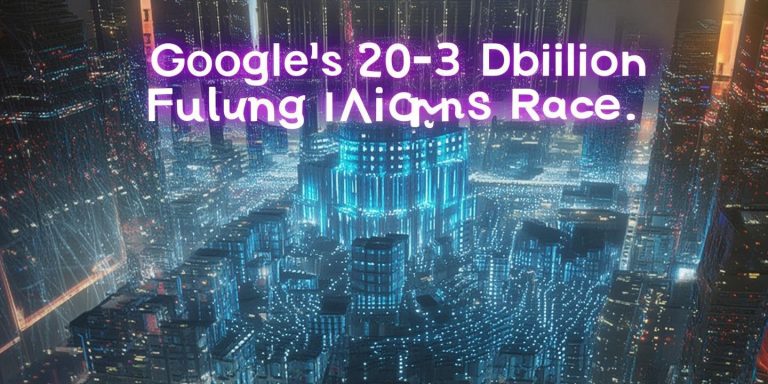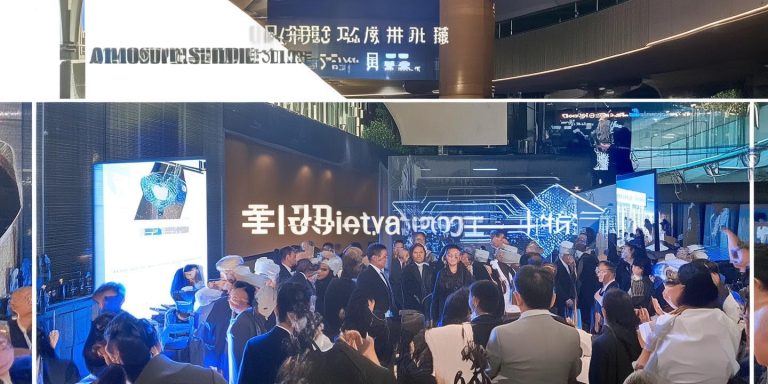编者按
近年来,PE/VC投资圈对”硬科技”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,但硬科技投资内卷的背后,却隐藏着项目估值虚高、技术”创新”与成果”转化”层出不穷的乱象。如何全面且专业地评估一个项目或技术的独特性、可行性及其市场化潜力,已成为各路投资机构面临的核心挑战。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又遍布荆棘的领域,作为行业参与者,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分享一些观点与思考,以抛砖引玉、集思广益,共同推动行业进步。”锲而舍之,朽木不折;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。”初心不改,坚持到底,正是最高形式的褒奖。
薛军(管理合伙人)
之路资本(El Camino Capital)二十年风险投资经验的资深创业投资家
影响”科技成果转化”的关键因素众多,包括时间、资金、市场环境及人才配置等。在上一篇文章中,我以Redlen的案例剖析了时间维度上的挑战,本篇将聚焦资金端的困境。我们认为:”科技成果转化”本质上是一个时间函数,而资金具有显著的时间成本属性,二者在时间偏好上存在天然矛盾,这正是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融资难的核心症结。
“科技成果转化”并非一个具有严格科学定义的概念,笼统强调其重要性缺乏现实意义。要深入分析这一问题,必须具体化、精细化。首先需明确区分”科学成果”与”技术成果”的差异。通常而言,这些”成果”主要源自大学及专业科研机构,而企业因目标导向明确、产业化能力更强,往往能更高效地推动成果转化。对于”技术成果”,只要具备市场价值与潜力,其产业化动力与能力相对充足,挑战性也相对可控。然而即便如此,一项关键技术的产业化周期往往以”十年”为单位计量,否则便难以称得上真正的高科技。
我的老领导罗建北老师,曾任清华计算机系党委书记。自上世纪90年代起,她便积极投身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事业,并参与创办了清华同方。针对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,她总结道:”大学科研成果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横向科研项目(企业或用户提出的),应用场景清晰,产品化与商业化相对容易;另一类是纵向科研项目(部委或专家主导的),这类成果转化难度极大,美国大学多采用’授权+收取使用费’的转化模式。这类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距离较远,即便投入大量人力、时间与资金,仍存在难以逾越的’死亡之谷’。”清华同方正是为解决这一转化难题而成立。

2003年我刚回清华工作时,陆致成老师便曾告诉我,清华的成果他们已全面梳理,能落地的同方都已实施。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”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”的产业化。该技术源于国家”八五计划”科技攻关项目(研发经费为国家资助),1996年1月通过国家验收。当时,法、德、英等国早已掌握该技术并形成产品,它并非重大科学发现,而是一项技术的应用落地,却仍经历了漫长的市场转化周期。在李岚清副总理的特别支持下,1999年底,同方首套设备才在天津东港海关正式投入使用。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东风,同方威视迅速发展,至2005年销售额突破10亿人民币,此时已历经九年。至今二十余年过去,这一案例仍是清华科技成果转化的标杆。清华控股公司大堂最醒目的位置,始终陈列着该产品的模型,足见其历史地位。
即便在清华这样顶尖的科研机构,真正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也屈指可数,难以持续产出,时常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。
而对于”科学成果”而言,产业化更是艰巨的挑战。首先需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,再谈产业化,而产业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创造巨大且潜在的市场价值,实现盈利并惠及大众。原华为投资部负责人陈崇军先生曾犀利指出:”大学的使命是金钱变知识,企业的使命才是知识变金钱。让大学搞科研变现,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。”
确实,大学的本质在于发现而非应用。真正高深的学问或重大发现,往往基于深刻的哲学思维,初现时看似无用或难以应用。要将这些看似无用的成果转化为实际价值,往往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。以爱因斯坦为例,1905年发表相对论原理,至1945年美国在广岛、长崎投下原子弹,已过去四十年。但原子弹爆炸并非科学成果转化的成功标志,因其能量释放不可控,仅能造成破坏而非造福人类,缺乏市场价值。直到1954年,世界上首艘核潜艇——美国海军”鹦鹉螺”号下水,人类才初步实现可控核能应用,但这仍是产业化的曙光。直至1957年,美国希平港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,才真正标志着相对论这一科学成果的转化成功。短短半个世纪,从理论到应用,跨越了漫长的道路。
若站在1905年讨论相对论的”科技成果转化”,无疑是荒谬的。但若无人推动科学成果向技术转化并实现产业化,”科技成果转化”的讨论又何其无趣?这正是其困难所在,构成了一种悖论。破解这一悖论的钥匙,唯有市场。没有市场就不会有投资。然而,人们对市场的期待普遍短期化,投资行为也追求快速或稳定回报,本质上是风险厌恶型。谁愿意为五十年后的市场或回报而投资?不求回报的出资或许存在,但那属于资助或捐赠,而非投资。

发达国家在此方面与中国并无本质差异。如Redlen公司,就获得了加拿大联邦及省政府巨额资助。我走访的欧洲高科技创业公司,多数依赖欧盟及本国政府资金,占比甚至很高,但仍是杯水车薪。缺乏商业化资金的持续投入,这些企业的生存都举步维艰。
当前,期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资,难度极大。若缺乏长期、稳定、特殊的政策优惠与法规保障,几乎无人愿承担风险。现实中,国有资产性质的科技成果要求保值增值,私人机构则更注重盈利。长期、未知甚至无回报的等待,难以持续。因此,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以回报为前提。但在这件事上,无人能保证必然盈利,即便愿意等待多年。那么,谁愿意承担风险?
因此,科技成果转化融资难是必然结果。若期待融资容易,便试图破解”既要……还要……”的逻辑悖论,而现实是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”,此问题无解。
薛军
2023年5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