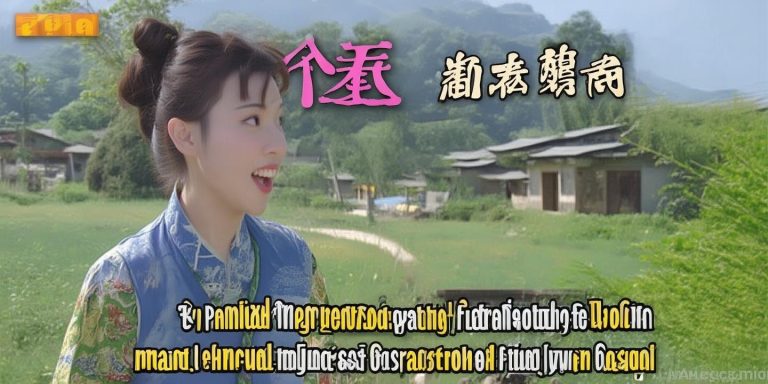Labubu旋风正席卷全球,其热度之高令人瞩目。近日,在永乐春季拍卖会上,一款薄荷色的Labubu玩偶以惊人的108万元天价成交。这款高131厘米、PVC材质的玩偶,生产成本不足千元,却足以抵得上京沪一套房的首付。几乎在同一时间,棕色Labubu限量版也以82万元的高价拍出。2024年,Labubu所属的THE MONSTERS系列收入从3.68亿元暴增至30.4亿元,增长率高达726.6%。
令人咋舌的二级市场溢价现象与这一数据相呼应。原价99元的隐藏款在二级市场上被炒至2600元以上;与Vans的联名款原价仅为599元,二手市场最高叫价却达到3.45万元;部分稀有款的溢价甚至超过1284%。这种狂热现象的背后,盲盒机制功不可没。泡泡玛特将隐藏款概率设定在0.69%(约1/144),精准利用了人类的赌博心理。正如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所言,用户购买盲盒收获了“15分钟的愉悦感”,这种体验“与赌场里的赌徒心态有相似之处”。
Labubu市场还呈现出明显的金融衍生品特征。在二级交易中,黄牛和“游资”扮演着做市商角色,通过囤货、抬价,影响全球Labubu定价。交易平台上甚至出现了“期货交易”——预售未拆封的高概率盲盒。更令人警觉的是,泡泡玛特本身也在进行“供需干预”。2024年双十一期间,官方大规模补货,导致部分款式价格短时间下跌30%-50%,这种操作与金融市场的做市商机制如出一辙。隐藏款的年均增值率已超过300%,远高于黄金和美国股市的年均收益率。
有评论认为,Labubu背后的不是潮玩经济,而是“类博彩经济”。这不仅让人联想起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,当时郁金香价格在一年内暴涨5900%。一株名为“永远的奥古斯都”的郁金香以6700荷兰盾成交,这笔钱在当时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。随后,1637年2月,当卖方突然大量抛售,市场瞬间崩盘。郁金香泡沫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,一种可以量产的物品,被人为制造稀缺并炒上天价。
类似的联想还可以有美国Ty公司的豆豆娃Beanie Babies。通过限量停产、情感故事包装(如附赠“出生证明”)和二级市场拍卖等方式,其稀有款“Princess the Bear”曾拍到50万美元,最后也因过度生产而崩盘。相比而言,Labubu的不同在哪里?作为工业化产品,东莞工厂的月度产能已达1000万只。当然,在“稀缺性+博彩机制+金融杠杆”之外,Labubu还有Z时代的消费替代、明星的加持、品牌与时尚的溢价、以及情绪价值承载等。
因为这些当代年轻消费者,追逐的不仅仅是一个玩偶,而是情感投射和自我表达的载体,是年轻人的“塑料茅台”,是他们的独特的“信仰测试”,更是人性对稀缺、归属与未知刺激的追逐。但这只是对当下现象的解释,而难以成为现象得以持续的支撑。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要素,都没有必然价值的内涵。除非,泡泡玛特可以不断推出下一个“Labubu”。当然,在这方面它不乏成功经验。在Labubu前,泡泡玛特的首个爆款Molly目前还生命力强劲,2024年销售额达20.9亿元。还有DIMOO,其曾与LABUBU交替成为泡泡玛特营收主力,通过联名(如迪士尼)和限量策略维等,生命周期有起伏,但仍在线。
国外成功经验则是,日本扭蛋文化。依靠20-50元低价盲抽机制,及成瘾性收集和社交属性等,从1980年代存续至今,而它也正是LABUBU盲盒的心理机制原型。可见,Labubu本质还是“新瓶装旧酒”的消费心理现象复刻。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,2024年泡泡玛特年会上,出场嘉宾郭麒麟说,“特别高兴能参加咱们境内最大的博彩公司年会。”满堂哄笑中王宁变了脸色,快速抢过话筒解释:“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潮玩公司!”看起来,这会是需要他不断去解释的一个梗。
而对于类似的质疑和不解,王宁多有论述,感兴趣可去查询。比如,他认为,所有的消费行为都是在解决两件事情:一个是满足感,一个是存在感。比如,他认为人的消费行为本质上是感性的,而不是理性的。比如,他说,“无用”的东西才是真正永恒的,“产品只要有了功能属性,都意味着生命周期的短暂和与生俱来的衰变”。这些充满哲学意味的洞察都有对的逻辑。问题是,这些论述与泡泡玛特和“Labubu”之间的必然关联又在哪里?